
烟业智汇

零售户在线

微薰

手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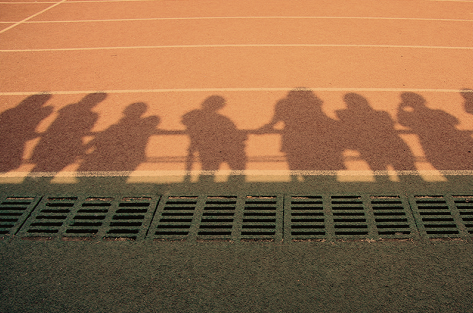
匆/匆/那/年
“红塔山”是我接触的第一个香烟品牌,我至今记得那天下午,被树叶筛下的阳光照亮半个宿舍,刚刚从操场上踢完足球回来的老五脱掉上衣,汗水打湿的上身好像抹着一层釉彩。他把自己横在床上,然后丢过来一支“红塔山”。
他是知道那时的我是不抽烟的,但他的动作是那么娴熟又自然,而我也鬼使神差地把它叼在嘴里,点燃了它。烟雾缭绕中,我被呛着了。老五笑了,好像我们之间捅破了一层纸。后来,我明白了一个道理,男人与男人之间就是一根烟的距离,跨过了这道坎就成了摔不烂的兄弟。

老五是个烟民,他平时是不吸“红塔山”的,作为一个囊中羞涩的大学生,“红塔山”是他的高配。我曾问他为什么吸烟?他说这是个没有答案的哲学问题,就像你爱一个女孩子,理由都是找出来的。假如你有求于他人,屡试不爽的敲门砖就是一包“红塔山”。吸着“红塔山”的老五陶醉的姿态像极了神仙,仿佛吐纳之间都是智慧的珠玑。他说,你看到了吗?这每一缕烟都是人的元气。它们袅袅上升,似与天接。
回忆起那段略带狗血的大学时光,假如没有“红塔山”,没有酒,似乎就欠缺了什么。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记忆往往不是画面,而是心境。“红塔山”作为性格的余数,既是一种装饰,也是一种外现。我曾用一包“红塔山”做酬劳让老五去讨一个女生的照片。后来,我们粘在一起了,不过是三人组合,我,她和老五。作为一个三人组合,我们一起熬夜看世界杯,当进球的时候,她会兴奋得揪自己的头发。我不知道她哪里吸引了我。爱本来就是盲目的产物。
有一天,她从我的嘴里抢下一支“红塔山”,装模作样地大吐烟圈。那模样让我想起电影里的阮玲玉。我以为她喜欢老五,但他们也没有走到一起,甚至连有没有爱过都是疑问。老五说,她是一个好姐妹,好兄弟。我捶他一拳,他装作龇牙咧嘴的样子。
但是我的心里依然难受。分手那天,老五陪我喝酒,吸烟。然后我们在校园里溜达。四月的校园充满了紫藤的香甜气息。他说你不应该选择萧瑟的冬天去追一个女孩儿。现在才是爱情发芽的季节。我一支接一支地抽“红塔山”,直到似晕非晕。他说:“暴敛天物啊,暴敛天物啊。”我看着“红塔山”一明一灭,犹如天空璀璨的星子。
一天,我和老五一起在宿舍看书,吸烟,聊天。突然门打开了,一个老师模样的人站在我们面前。我和老五慌不迭地把烟藏在身后。那人说,“别藏了,我在门外就闻到‘红塔山’的味道了。给我一支解解馋,快憋死我了。”他是林老师,著作等身。后来,我们成了忘年交。我问他学问之道。他调侃道,“李白斗酒诗百篇,没有烟卷写不完。”一个认真的回答是,当他灵感枯竭的时候,一支“红塔山”就可以解他的燃眉之急。

那时,我疯狂地迷恋一本书,海里因希•伯尔的《无主之家》,里面有一个家庭主妇,忙活完了,就会点燃一支烟,躺在床上读书。不知道为什么,这个镜头始终铭刻在我的脑海里。在我的想象里,她夹在指间的就是一支“红塔山”。
“红塔山”,我青春的第一支烟,也是我和兄弟分享的烟,是我的大学记忆,正如那些我读过的书,塑造了今天的我,也成为我的最爱。它的经典是无惧潮流的笃定;它的经典是品质之上的恪守。
得知“红塔山”即将上市一款新烟“红塔山(大经典1956)”,我十分欣喜。心想着,它定是穿越了时空,只为和我相见,我似乎等来了许久不见的朋友。
2020年,我等来了“红塔山(大经典1956)”好品新升级,我似乎又回到了我的青葱岁月,回到了那个友情与爱情都在身边的星光璀璨的夜晚。

